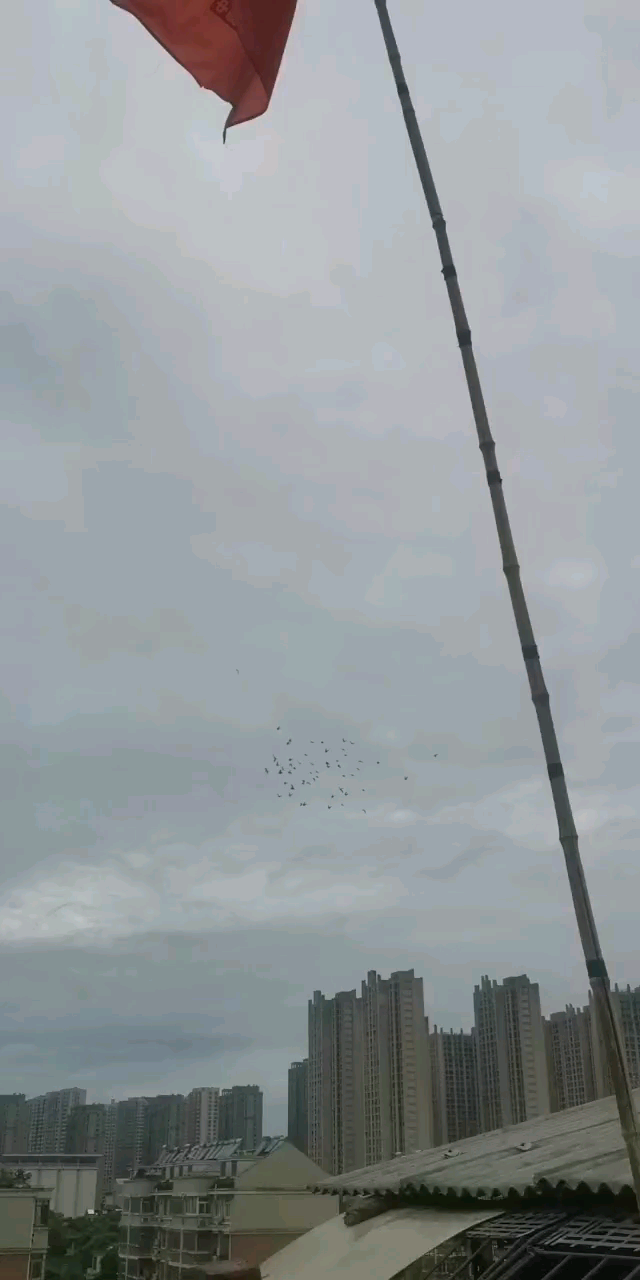咕咕……咕……一阵婉转的鸽子叫声传入毛阿婆的耳际,她抬头一看鸽笼,一群鸽子活蹦乱跳地叫个欢。好几只鸽子簇拥在毛阿婆养的母鸽旁边,亲热得摇头摆尾。毛阿婆看着亲密无间的鸽子,露出久违的微笑。
毛阿婆年轻时长得如花似玉,是方圆十几里有名的大美人。年轻时与一位后生偷吃了禁果,高不成,低不就,嫁给了渔夫严广济。毛阿婆做姑娘时就喜欢养鸽子,嫁到里塘村后,养鸽子的兴趣不减当年。
毛阿婆早年丧夫,母子相依为命,她把鸽子当作自己倾诉的对象,逗逗鸽子,说说话,平平淡淡地过着日子。
这是谁家的鸽子?正在毛阿婆疑惑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走了过来。这个老人就是临村的严阿公。
严阿公年轻时被国民党抓走了,几十年不见音信。今年孑然一身突然从台湾回来,至今没有结婚。听人说,严阿公年轻时是捕鱼能手,曾经跟附近高阳村的一位姑娘好上了。
毛阿婆定睛一看,嘴巴长大了,好久没合上。严阿公也看见了,目瞪口呆。
是你。
是你。
两位老人同时说着同样的话,心里却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久久难以平静,太出乎意料了。这不是魂牵梦萦的昔日恋人吗?真是一场梦,几十年的梦呀。两位老人握着手,任凭泪水悄悄地流,纵有千言万语也说不出一句话,心像刀割一样痛。
严阿公的鸽子依然飞到毛阿婆的家,整天呆在鸽笼里,一唱一和地玩个欢。毛阿婆把严阿公的鸽子当作自家一样,精心饲养。严阿公有事没事都会来毛阿婆的家,看看鸽子,说说话。说着,就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年轻时铭心刻骨的一幕,谁也不说话,沉浸在温馨的遐想之中。
毛阿婆的儿子在县城工作,觉得母亲一人在家寂寞冷清,就把母亲接到城里颐养天年。毛阿婆不愿拂去儿子的心意,跟严阿公交代一番,依依惜别,跟着儿子来到了县城。
刚到县城的几天里,毛阿婆在儿子的陪同下,逛公园、游商场,把城里的好去处一一游览个遍。可是,儿子工作忙,不可能三天两头陪着她,尤其是孙女去上学,宽敞的套房里只有毛阿婆一人了,她感到很孤单。
城里不像农村,家家户户都是铜墙铁壁,连找个唠嗑子的人都很难。毛阿婆只能看看电视,听听越剧,索然寡味地过着日子。这样过了半个月,毛阿婆觉得烦了,心里闷得慌。她经常做梦,梦境都是严阿公孤零零地站在村口,手搭凉棚,痴痴地张望。
毛阿婆想起了家里的鸽子,想起了严阿公。一想到严阿公,毛阿婆的脸上显出一分激动,几分牵挂。毛阿婆看着外面熙熙攘攘的人流,回到乡下去的心情日益滋长。
吃晚饭时,毛阿婆几次张口又闭上了,说心里话,儿子、儿媳对她很体贴,生活照顾得很周到,没有她劳心费神的事。自己怎么说得出口呢?万一儿子误会了咋办?毛阿婆有心事,吃饭也心不在焉,机械地扒拉着,缄默不语。
儿子看着母亲异常的表情,知道母亲有什么话要说,就小心翼翼地问,妈,你有话就说吧!毛阿婆看着儿子,摇了摇头,欲言又止。
妈,你说吧,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改正就是了,不要憋在心里。儿媳接着话茬说。毛阿婆看着儿子和儿媳,眼圈微微发红,掏出手帕捏了捏鼻子,脱口而出,我想回家。声音轻得像蚊子叫。儿子和媳妇听了,不明就里,怔怔地互相看着。
母亲态度坚决,儿子也不执意挽留,决定明天送她回乡下。
第二天一大早,一家人有说有笑地向车站走去。毛阿婆真是乐坏了,脚步松爽,眉开眼笑的,饱经风霜的脸上洋溢着喜气。儿子把母亲扶上车坐好。毛阿婆探出窗口,挥着手,脸上像盛开着的菊花。
毛阿婆乐颠颠地回到家里,看见严阿公正在拾掇着鸽子笼。严阿公,我回来了。严阿公见是毛阿婆回来了,喜出望外,手在衣服上擦拭几下,接过毛阿婆的包裹,咧开嘴巴笑了,笑得很舒心,脸上显出惊喜的神色。
春节前夕,儿子带着一家三口兴高采烈地看望母亲。刚到村口,有人说了不阴不阳的话,儿子早有耳闻母亲跟严阿公有点出格,听着村里人说三道四,脸立即晴转多云了,阴森森得吓人。
儿子到了家,果然看见母亲跟严阿公有说有笑地聊个不停,亲亲热热的,儿子的脸拉长了。严阿公看见了,喜形于色,眼睛露出久违的亮光。儿子没有理睬严阿公,装模作样地笑着说,妈,我们是接你到城里过年的。
毛阿婆一听,脸色发白,百般争辩,我不是过得很好吗?不去。再说,我走了,鸽子谁来养?儿子一听到鸽子,气不打一处来,随手拿起一把刀,三下五除二地把鸽子宰了。鸽子扑腾着,哀鸣着,殷红的鲜血从脖子上一滴一滴地落下来。
毛阿婆看着滴落的血,好似有人刎着她的心,鲜血从心中往外汩汩地流淌。严阿公默默地离开,不时地摸眼泪,叹着气,身子显得更苍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