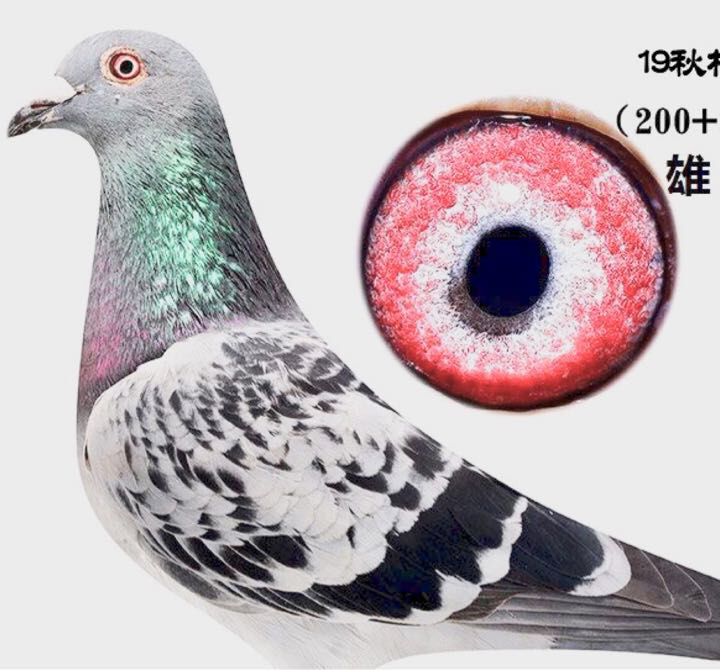鸽子,我的一段缘
几经何时,不经意的我无意中接触到这个透着灵秀、干净而优雅,一生忠贞不渝的精灵,它们身上的羽色,不管是深雨点,还是浅雨点、绛红、灰二线、红二线,或是垃圾灰还是纯白,每一种羽色华美并不艳丽,清秀雅致不沾一点庸俗。
那是广东汕头,当黎明呼唤朝阳慢慢爬过翠绿的山峦,微风下蔚蓝的大海翻着浪花,召唤有些懒散有些懵懂花草,“咕咕”的叫声将沉睡中的我从梦中拽了起来。有些迷糊有些好奇的我打开阳台的门,噼里啪啦的翅膀煽动的声音,和远处军号和雄壮的部队的早操声,让我从没有清醒朦胧中定了定神,几十只各种颜色鸽子都飞落在鸽笼的高处,警惕的观察我这个陌生人,几平方的阳台上下排了几排鸽巢,地上有一个饲水器和一个饲喂槽。对它们来说,陌生的我可能打扰了它们的早餐,它们在鸽笼最高处仍然警惕的躲避我,好像随时都可以飞走,也只有在产巢里孵化育婴的鸽子,仿佛不屑的白了我一眼继续做自己的事。
我小心翼翼地退了出来,趴在玻璃上看着它们 ,随着我的离开,好像我的惊扰并没有影响到它们,它们展开炫丽缤纷的翅膀纷落到食槽和水槽旁边,悠闲优雅地进食饮水,公鸽鼓起颈上最绚丽鲜艳羽毛,嘴里一边“咕咕”的叫着,一边追逐着心目中的偶像。“咕咕”的叫声仿佛是吟唱,是述说爱恋和忠贞不渝,因为鸽子一旦配对如果不是人为的改变,那是终其一生的伴侣。在鸽笼的上方,一只公鸽在给自己的妻子梳理羽毛,就好似眷恋中的相濡以沐,母鸽静静地蹲在那里,温柔依偎着这份温情,享受着这份爱恋,而它们的旁边一只鸽子,来回走着另一只鸽子饮完水飞落它的身旁,用嘴轻轻在它绚丽颈羽上滑了几下,随后便热吻了起来,看到这一幕让我有些惊讶了?“鸽子接吻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二哥说着走进鸽笼,让人感动的是十几只鸽子,一下子飞到二哥的身上,就像孩子看到父母一样,扇着翅膀爬到肩头落到手上和头上。
这一幕让我羡慕,灵性与情感交融精灵,看到主人亲近后,便飞落到放飞的笼门前,在等待着蓝天那宽阔博大的胸怀拥抱,也或是展开翅膀的它们敞开自己的胸怀,去容纳白云。
时光的长河流缓缓淌间,披着一身浅色的红雨点羽毛,尽显高贵优雅,款款相携漫步来到这个时空,而更让它们高傲的是它们的儿女,不仅在巴塞罗那的比赛中摘下璀璨,还在马赛艰苦恶劣的赛程上展开优美的翅膀,飞出令人羡慕一缕彩虹。红狐狸的名字洒脱在一个时代黄金配对,让它们的主人比利时詹森兄弟,在拥有财富的同时,也登上了信鸽育种金字塔的巅峰。
造化弄人荷兰杨阿腾,在离开这个世界的几十年后,冷艳清润墨雨点赛鸽,它们犹如闪电在地中海上展翅让浪花飞舞,它们宛如流星穿破阿尔卑斯山乌云和雾雨,欧洲各大远程赛事中,不断地安慰已经远走的主人的亡魂,也让荷兰这个以风车闻名于世的国家,又添赛鸽故乡的雅号。
距比利时、荷兰遥远万里的中国,随着中国雪兰鸽诀别离去消萧香玉陨,让这块古老的大地上信鸽的品系成为绝唱。时光荏苒来到了民国,李梅龄在画桥烟柳水榭楼台的上海,杏雨朦胧中与几只德国信鸽不期而遇,雄唱黄浦江两岸十里洋行的上空,也为几十年的后世写下一篇让人荡气回肠,被世界鸽坛称为残忍的炼狱超远程赛事。
如果两千五百公里的疏勒河,让大部分国外的赛鸽望而却步,那么更远的十三间房,那里有风沙弥漫的大漠,犹如一缕孤烟伴随着落日余映满天的晚霞,飞向遥远那小桥流水的江南。苍凉的月光下,岩壁、树林或是戈壁里的一块石头,都是它们警惕中的暂时安然,它们牵挂的是鸽巢里还没孵化的孩子和那个让它梦绕的伴侣。或许,明天就成为鹰隼早餐,或许,没能躲过栏在半空的天网,或许,没有食物和水,让它们永远的留在这残酷而艰辛的异乡。然而,即使有惊人的毅力,机警的智慧,矫健的体魄,可绝大部分鸽子没有回到那个它们心中的温巢。
上海,城隍庙赛鸽集市上,一个小鸽笼,羽毛蓬松让它有些疲倦,消瘦的体魄也没有曾经的俊郎,萎靡的状态,有一双有神的眼睛也尽显疲惫,也没能引人们注意。“这只是有李种血统的拖拉机罢了”,很多人摇头,有人叹息,当有人上手观看,看到红红的鸽环上的号码时,“小蛮牛”十三间房的冠军!惊叹中让几十个鸽友瞬间围了过来,每个人都带着崇敬,带着惊叹没人移动离开的脚步,仿佛这一刻都忘记了鸽子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