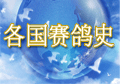明清时期的赛鸽和赛鸽会
我国从明代开始,逐渐把传信鸽用作比赛鸽。由于宋代信鸽的大量增加,其中用于传书的只是极少数,而大多数作为玩赏。鸽主在用信鸽传书时,有些信鸽在途中游失它乡而不能归巢,这是常事。所以鸽主主要用三五羽,甚至十几羽同时放飞,归巢时有的率先而归,有的则姗姗来迟,也有杳无音信的。于是引发了一种比一比传书快慢的构想,赛鸽活动就随之产生了。
明朝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在苏北淮阴一带,有一天风雨交加,有一羽鸽子掉落在屋顶上,显得十分疲乏。当被屋主捉住,正准备杀它时,主人发现鸽足上有一件用油纸封裹的信件。屋主看了信封上的字,知道这羽鸽子是从北京飞来的,时间只有3天。北京到淮阴,空距七百多千米。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五百多年前的信鸽已有很高的归巢水平。就鸽主来讲,这羽鸽子是飞失了,如果他同时放出多羽,那么有的鸽子可能已经回归家园。如果单放一羽,他就会从中吸取教训,下次放鸽传书就要多放几羽。
明清时期,是信鸽发展成赛鸽的转折时期,发展最早的地区,首推广东一带。当时广东存在的佛山“飞鸽会”、广东“赛鸽会”和“白鸽会”,可以作两种推测,一是纯属赛鸽组织;一是鸽子比赛的会期。从一些记载的史料来看,后这的可能性较大,但从这些完备的赛鸽活动的章程来看,一种帮会式的松散的赛鸽组织的存在,也是有可能的。所有这些,与今天的信鸽比赛有许多类似之处。广东番禺人屈大均(1630-1696年)所著的《广东新语》(卷二十“鸽”)有这样一段叙述:
“广东人有放鸽之会,岁五六月始放鸽。鸽人各以其鸽至,立者验其鸽,为调四、调五、调六、调七也,则以印半嵌入翼,半嵌于册以识之。凡六鸽为一号,有一人而印一二号至十号百号者,有数人而合百号者。每一鸽出金二钱,主者贮以为赏。放之日,主者分其二,一在佛山曰内主者,一在会场曰外主者。于是内主者出教,以清远之东林寺为初场,飞来寺为二场,英德之横石驿为三场,期以自近而远。鸽人则以其鸽往,既至场外,主者复印其翼乃放鸽。一日自东林(寺)而归者,内主者验其翼印不谬,则书于册曰:‘某日某时某人鸽至’,是为初场中矣。一日飞来(寺)而归,一日自横石(驿)而归,皆知前验印书于册,是为二场。三场皆中,乃于三场皆中之中,内主者择其最先归者,以花红缠其鸽颈,而觞鸽人以大白,演伎乐相庆。越数日分所贮金,某人当日归鸽若干,则得金若干。有一人而归鸽数十者,有是人千鸽而归一二者。当日归者甲之,次日归者乙之,是为放鸽会。”300多年前“佛山放鸽会”的赛项竟与今天的3关赛一模一样,第一关,清远东临寺到佛山的空距是75千米,第二关飞来寺为95千米,第三关英德横石驿为155千米。这是欧洲200多年以后才达到的水平。
清乾隆年间,苏州也有放鸽会,有“红脚鸟跟人飞,碧云照凤凰翔”之说,姑苏人常用这样的话语来形容养鸽人和放鸽会的情景交融。那里的养鸽者把信鸽和观赏鸽混养一起,常见的有“银白底”、“紫球”、“白丝筋”和“白砂”等观赏鸽,一些“铁砂”、“浙江灰”和“点子”等飞翔鸽作为名贵鸽种,每到五六月间举行放鸽会,届时养鸽者聚集一起,开笼放鸽。蓝天中白顶紫羽,五彩缤纷,鸽主们登高览望,赏心悦目。有些鸽主的观赏方法别具一格,他们在放出鸽子后,围坐在一盆清水或一方大镜子前,无需抬头,只是俯首观看鸽影,真是别有情趣。在北京、南京、西安、开封、洛阳和杭州等古都,都有形形式式的放鸽活动。特别是北京,鸽主们都把鸽哨系在鸽尾上,鸽子在蓝天飞翔,哨音遍及大地,时宏时细,时远时近,真有“疑是仙乐落九天”之感。
明末清初的赛鸽在南方较盛行,而《鸽经》却产生于黄河入海处的山东。由此可见,当时的养鸽、赛鸽并不限于广东,而很可能遍及神州大地。
《鸽经》共分“论鸽”、“花色”、“飞放”、“翻跳”、“典故”和“赋诗”等六章,是一本比较精练的养鸽全书。在“飞放”一章中,较详细地论述了信鸽的品种特色。
《鸽经》作者为今山东省邹平县的张万钟。据考证,他的生卒年代是公元1592-1644年,成书时间约公元1622年。据国外资料记载,世界上最早的养鸽著作始见于1780年,而《鸽经》早于他们158年。
当时的山东,养鸽之盛,有一则资料可作佐证。山东曲阜孔子的大弟子颜回四十八世颜清甫,久病卧床,他的幼子偶然弹伤一羽鸽子,想给父亲补补身体,宰杀时发现鸽子羽毛中间有一封书信,上写:“题云家书付男郭禹”,这是郭禹的父亲写给他儿子的信。郭禹原是山东曲阜的地方官,这时已调任去远平府上任。颜清甫命儿子把死鸽和信件一起松动远平府郭禹处。郭禹见到鸽子和信件后凄然地叹道:“畜此鸽已十七年矣,凡有家音,虽隔数千里,亦能传至。”说罢就命家人把死鸽埋葬了。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羽超远程赛鸽,但竟是一羽十七年鸽龄的老鸽子。史料中的“数千里”和“十七年”,可能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但它确是一羽优良的信鸽。
——节选自《新编信鸽手册》(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