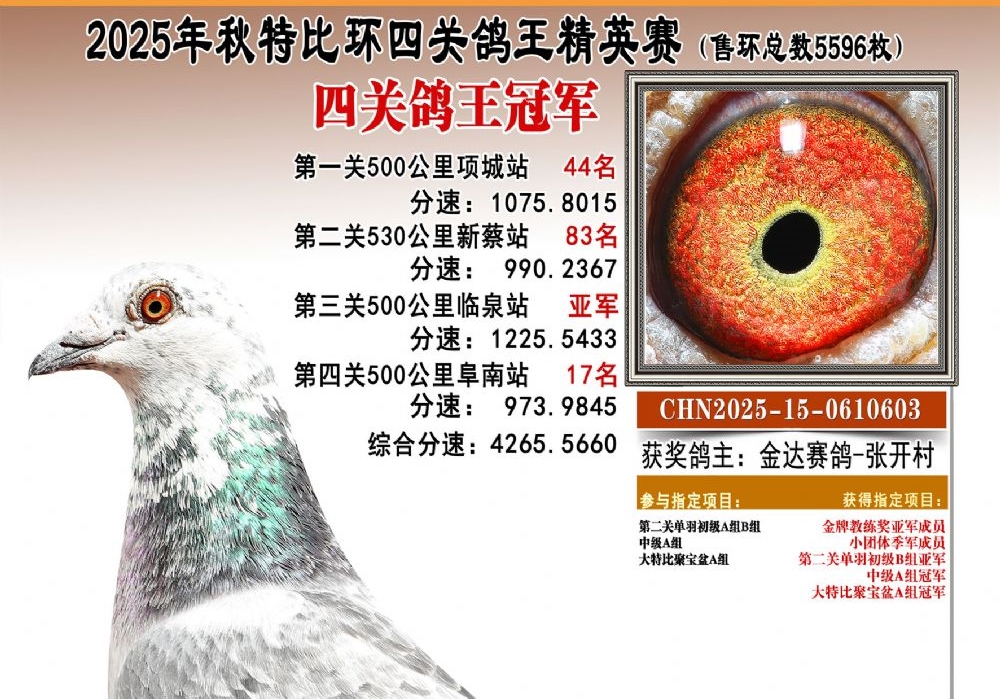注:这是老早写就的一篇鸽事杂文,后来在多家文学论坛和网站被多次加精,读者反响强烈,再掉转头去看这篇文字时,有鉴于我以前有过对鸽子的戳杀行为,在此做出忏悔,并呼吁鸽友要以此为忌。欣慰的是,现在我已经不那么干了。

渐渐的,我的飞行队伍成了村落日下的一道风景,做伴夕阳引领暮色中的炊烟,自由自在无处不在,扇动入夜的风。在前门,我也被老北京这种很传统的情状吸引着,感动着,追随着。在我看来,这是北京的一种风味。鸽子带哨盘飞的景象,哪儿也比不上北京城——老新影剧渲写之下,仿佛俯身老的四合院建筑群中才算正宗。我到时是七月,鸽子开始换羽,所以就听不到鸽哨响,只有那样的盘旋依旧,此情此景,几乎无处不在,故宫,世界公园,天安门广场,表姐住的西罗园,人到鸽在。高高的楼,半天高的鸽舍,由此及彼,星星碎碎地挂出了北京的人鸽情怀。
忙里偷闲,我到西罗园一位鸽友家坐了坐,他住16楼。我敲门时他正吃饭,桌上摆着四五样小菜,抿着酒一个人喝。我告诉他儿子来历:看看鸽子,立马就被放进去了。他挺热情,一口京片子,问我吃饭没?我说吃过了,每天都在你早晨清扫鸽棚的声音中醒来,知你管理有法,想来鸟也不至于坏,就上来看看。他说瞎胡弄,就带我上阳台进舍。对他的鸽子印象不是很深,深的是他客厅最显眼的地方被几尊奖杯所占据,挨窗户一大块地方簇着整袋的鸽粮,砂土,大小各异的鸽笼等物。凭着这样的排场,周围有点年纪的同志管我们叫浪荡公子哥儿——咱得服气,还得顶上这个帽子,别忘了,这也算代价——其实,有它们做铺垫,我们活得挺好,这叫乐有所靠——管你帽不帽?
西罗园小区,除了人多房子多,就数狗多,各种各样的狗,品种纯贵,洗得也干净,它们和我们身边的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语,正如村子里的生活比不上北京。我做了一些调查,北京的足环一枚是三元,比我们贵了两块。那里的衣服很露,露得一片肚脐眼,还有肚脐眼以下的一巴掌,毛重的人休想穿出来,除非人家真敢。
在北京还有一个感触,就是西单是一块容易让人忘乎所以的地方。听说了有这么个地方,勾起了我们前往的脚步。神交,想开眼,由耳膜始。我用自带的相机留住了西单,带回了西单,中间有妻子,二婧还有丈母娘。单把我落下了,我在她们对面站着聚焦,也聚焦了一个关于西单的传说。西单最大最久的传说是价格,天价,让你回头掉头,扬眉蹙眉。一千块个把裤衩,就叫西单。
几天下来,凭心而论我最喜欢的还是紫禁城,如果说人死后最耐糟最耐沤的是把子骨头,那么老北京糟沤来糟沤去保存最好最完整的就是这个部分,虽然很多经过了人为的修复和重塑。我游历的紫禁城正大演修复法,重塑法,很多建筑被脚手架网起来,重修的技艺,就像是蜘蛛。
回来看故宫的专题片,那上面尽显了故宫文化最简单又最复杂的脉络,有横线,有竖线,有相交了的线和平行线,也可以凑成蜘蛛网,所以,艺术行径就是蜘蛛行径,想来下子艺术,就得当回蜘蛛。
在这个专题片的剪辑当中,有一个就是掠过朱红砖墙的鸽影,一晃而过,还有高墙西迁的深影。某一小节还在西太后储秀宫廊下放开数羽鸽子,它们在那儿起飞,不免毛羽零落,以此显现一个伟大王朝末路的掠影。这个王朝叫清朝,开国时它备了二十五枚皇印,想以此比肩汉代,可惜比不上,没用到一半匆匆落幕,西太后,乾隆爷还曝尸荒野。
谁拔了人家的毛?
我该拔谁的毛?
写这段文字的间儿,我用鸽网扣死了一只游棚的灰鸽,摘下它时残羽纷纷。我敢拔谁的毛?我有种痛,尤其看到它临死挣动的样子。前院的王老太迷信鸽子肉治她多年的“腿阴风”(风湿病,只有她这么叫,不过,她后来死了,把她的怪名儿一起带走了),我就拿它献礼吧!
在西单,在故宫,只要有消费,我就是给人拔毛呢。北京的某个口袋一定还有我的残羽,只是当着一地的鸡毛,谁知道哪片是谁的?
生活就是在拔与被拔中跳舞,或者荡秋千。
生活了才认识,认识了生活还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