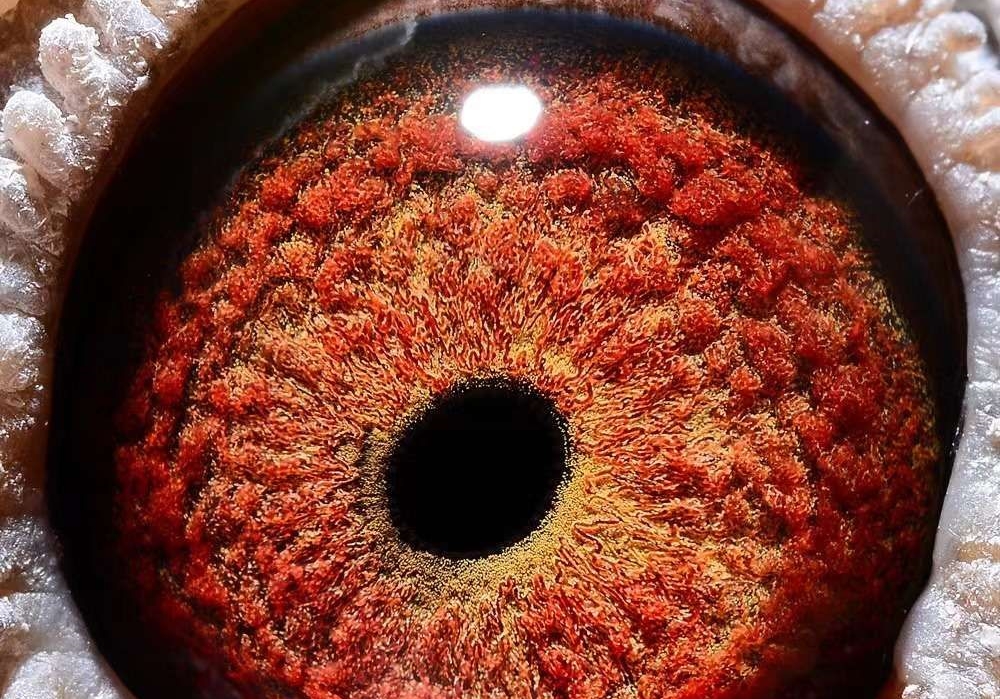孩子走后,中年人又躺在了摇椅上.他不多久就睡熟了,梦见小时候见到的东韩的天空,宁静而深邃,还有大片的麦地和绿色的稻田。他如今每天夜里都回到那片田野间,在梦中听见清晨农机耕地的隆隆声和部队营地传来的起床号,看见农民驾马车穿行于林中小路。他睡着时闻到田野上青草和泥土的气味,还闻到早晨田野上刮来的风带来的平原气息。
通常一阵北方特有的季风吹过,就会让他醒来。可最近他常常闻到一股湿湿的咸腥味道,伴着一种隐隐如从天边传来的轰鸣声,他在梦中知道时间尚早就继续把梦做下去,看见在小树林的旁边是一大片响着蛙鸣的绿油油的稻田,其中还有蛙声响成一片的几洼荷塘,随后梦见了东韩的各处街道和建筑物。
他不再梦见坠楼,不再梦见女人,不再梦见伟大的事件,不再梦见追杀,不再梦见人在旅途,不再梦见他的父母。他如今只梦见一些地方和天空中的飞鸟。它们展翅从高空俯冲向宽阔的水面。一只翅翼如垂天之云的黑色大鸟,擦着小树林的树梢无声地掠过。他爱它们,如同爱这孩子一样。他从没梦见过这孩子。
天一亮,当鸽子鸣叫的咕咕声将中年人从梦中惊醒,睡眼惺忪的他恍惚地意识到从此将迎来每一个没有孩子做伴儿的早晨。
他将鸽子从棚中放出,开始从井下汲水。这在孩子做来十分轻松的动作,在他却显得有些吃力。“难道我老了?”他说出声来。“不。我还不老。我只是不经常做而已。”
他试着用左手做事,这一次从井下汲水也是一样。从地下二百多米将水汲上来,即使有辘轳帮忙,也需要有相当大的力气来摇动提升。
他喜欢用左手做事。他只有这两只手,但左手总是不听使唤。左手腕在用力时常常会抽起筋来,这让他有些气恼。这左手握着辘轳的摇把在用劲,他厌恶地朝它看着。他在摇着辘轳,汲水的水桶在升到井深一半时,左手腕突然一阵疼痛,他赶紧换了右手扶住摇把。不然不听话的左手一松,倒转的辘轳就会将一桶水抛下去。他更相信自己的右手。
“这叫什么手啊,”他说出声来。“如果你想抽筋,那就去抽筋吧。让你变成一只鸟爪,看看会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恨抽筋,他想。这是在与自己的身体为敌,由于穷困而无钱买手机或者因为喝醉而呕吐,会让别人看不起自己。但是抽筋却让自己看不起自己,尤其是当一个人独自待着的时候。
要是那孩子在就好了,我的左手腕也不至于此,他想。不过这疼痛总会过去的。
“我该去洗漱了,”他说出声来。“之后才好喝点这口深井里的天然水。它对治愈我的抽筋有帮助。”
他记不清自己从何时起开始在独自待着的情况下自言自语的。往年他独自待着时喜欢情不自禁地唱歌,有时候冲着淋浴唱,那是在因出外写生和旅游而入住客栈时的事。他也许是因为那孩子走了,才在独自待着时开始自言自语的。不过他记不清了。这会儿他对自己说着心里想说的话,这样说出声来已有好几次了,这种情况只发生在没有人受到他说话干扰的环境。
“要是我这样自言自语的,别人听到后非把我当成是个神经病不可,”他说出声来。“不过既然我没有神经,我就不怕,还是要说。别人养鸽子有鸽友陪他们说话,还把公棚赛的消息告诉他们。”
现在可不是思量公棚赛的时刻,他想。现在只应该思量一桩事。就是我生来要干的那桩事。这条壁画上的龙很可能在等待着什么,他想。我在夜里睡觉时感觉到了来自远方的气息。鸽子在空中飞得很高,飞得很疾。今天凡是在这个院中筑巢的鸟儿都飞起来了。它们在庭院上空旋转不止。难道有什么难以预见的事情要发生吗?也许,这是什么我不懂得的天气征兆?
在这座宅院庭前生长的菩提树和梧桐树上,高大茂密的树枝之间筑起了许多鸟巢。鸟儿们拉下的粪便遍布庭前石地,这也是中年人每天早上打扫庭院的内容之一。在这些鸟儿当中,以喜鹊和斑鸠为主,还有几种叫不出名的鸟儿。
对于披着黑白或灰白外衣,经常站在树上翘动着长尾巴嘎嘎直叫的喜鹊,他持以中性的看法,既不喜欢也不讨厌,任由它们在树上折腾。他并不认为这种乍一看犹似乌鸦的鸟儿会给人带来什么好运,“它不过徒有其名而已,”他说。
他喜欢褐色的斑鸠,它们形态优美,飞行迅速,价值很高,是鸽子的近亲。
他不知道在这个城市里随处可见的麻雀都在哪里筑巢,它们从前是在平房的屋檐下筑巢,现在平房都变成了楼房,它们会在哪里筑巢呢。他对这种专吃人类剩食,大量存在、其貌不扬的鸟类抱有一种不怀恶意的轻蔑。同时,他又惊叹于这种鸟类适应环境的超强能力。它们不怕人,每天叽叽喳喳,三五成群地蹦跳于人们的脚下,显得快乐而满足。
他最喜欢的是偶尔在天空中盘旋的鹞子,它是天空中孤独的王者,也被称作是鸽子的天敌。它目光犀利,能从高空发现一万米之外地面上的猎物,然后从空中划出一个漂亮的弧线直扑下去,以一对强有力的利爪致对手于死地。
每当天空中有鹞子出现,地面上的一群鸽子总会不约而同,一动不动地向它行注目礼,并伴有节奏感鲜明的打嗝儿声。从鸽子仰望着鹞子投射出的眼神里,中年人读出了一种对比自己强大和崇高的同类所产生的敬畏感。
如果这时也有一群鸽子正好在鹞子盘旋的天空附近飞翔,在地面上的他虽看不到鸽子的神情,却能从鸽子飞翔的姿态上看出,它们并不真的惧怕这位天敌。只见鸽群围着鹞子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地上下飞行,大有与鹞共舞之意。鹞子呢,似乎对身边飞行的鸽群并不感兴趣,依然从容不迫地盘旋。
“它们都是好样的,”他说。“它们嬉耍,追逐,和而不同。它们是我们的兄弟,就像斑鸠一样。”
“鸟随鸾凤飞腾远,”他说出声来。“我应该记住在吃过乳糜后,就在凤的壁画上再画几只鸽子。好让凤保佑我的鸽子不同凡响。”
他坐在树下,一边喝着茶,一边看着画有凤的壁画。
跟着他怜悯起另一侧墙壁上看起来只有头和尾巴的龙来了。这是一条多么出色和奇特的龙啊,他想。又有谁知道它的年龄呢。我从没接触过这样强大的龙,也没见过能隐形于墙壁上而潜伏不动的龙。也许它太害羞,不愿从墙壁上现出原形。它可以从墙壁上现出原形,或者来个猛冲,把我和墙壁搞垮。不过,也许它曾被擒住过好多次,所以知道应该如何搏斗。它哪会知道它的对手只有一个人,而且是个单身汉。不过它是条多大的龙啊,如果龙形逼真的话,再配上这座老宅一齐开放接客,能卖多少门票啊。它引着画笔走时像条真龙,藏着不动时也像真龙,较量起来一点也不惊慌。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想法,还是就跟我一样地舍命相搏?
他想起有一次在冬季飘着大雪的一天,一只足环上粘有比赛标志不干胶的白色雌鸽中伤落在院中的雪地上。白鸽胸前的伤口渗出的鲜血染红了地上的白雪,像是开在雪中的红梅。那只与白色雌鸽相随的白色雄鸽落在院中的墙头上呜呜地呼唤自己的伴侣。它待了一会儿起飞,在院子的上空盘旋几周后又落在院子三层楼的飞檐上。跟着,当中年人忙着拾起雌鸽、为它治伤的时候,雄鸽从屋檐上飞起,围绕着院子忽高忽低的旋转,看看雌鸽在哪里,然后又落在飞檐上,呜呜地鸣叫。它那在空中疾飞的白色身影,实在正是白色的精灵,而忽开忽合的翅膀,又分别像天使在飞翔。它是美丽的,中年人想起,而它始终待在那儿不走。
中年人想:这是我看到的最伤心的情景了,孩子也很伤心,因此我们请求这只雄鸽理解,雌鸽的伤能快点儿好起来。中年人将这只受伤的白雌鸽抹上药后单独关养。伤好后将其放开。它,在院子的上空盘旋几周后离去。三天后,它带回了那只白雄鸽。
当这对去而复返的白鸽回来时,它们只是落在墙头上观望,没过多久就飞落院中,与棚中的其它鸽子相互追逐嬉戏。从此,这对白鸽就在每天早上必来,看到棚中的其它鸽子洗澡,也会加入其中,跳入浴盆洗浴,然后在下午时分又飞走。
中年人想留下这对白鸽很容易,但他选择的是顺其自然,既不驱赶,也不强留。
按说像这种参加比赛的信鸽,它选择的是飞行在高远的天空中。即使不得已在中途饮水或是过夜或是觅食,也应远远地避开一切圈套、罗网和诡计,甚至是被当作天敌的鹞子。这是对一只鸽子是否具备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的考验。否则它很难顺利归巢,回到焦急等待它回来的主人身边,更不用说摘金夺银。但现在这对白鸽却是这样。
不过,他想,我总是把鸽子自然地放在适当的地方饲养。问题只在于我的运气就此不好了。可是谁说的准呢?说不定今天就转运。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日子,走运当然是好。不过,我情愿做到依其本性。这样,运气来的时候,你就水到渠成了。
有时候,中年人很想搬梯子上树,看看鸟巢里面的鸟蛋和雏鸟。他并不想掏鸟蛋吃,而是对鸟类育雏感兴趣。尽管他曾多年在野外掏过鸟蛋,甚至吃过雏鸟,为了健脑和使身子长力气。他在五月份连吃了整整一个月,使自己到六月份能头脑清醒,身强力壮,去画地道的龙和养好鸽子参加千公里大赛。
他从前吃过不少雏鸟,甚至是自己的鸽子。大多数鸽友厌恶这种鸟类熬在汤里的味道。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种汤却对防治一切伤风流感都有着非常好的疗效,而且对眼睛也有保健作用。
他如今已不吃这些东西了,他只对鸟类育雏感兴趣。
为了保养体力画壁画和养鸽子,中年人只喝水和在早上吃一碗乳糜。他知道这是他一整天的饮食,应该把它们消化了。长期以来,他已经厌烦了吃饭,因此从来不准备午饭。他往往在早上吃一碗乳糜,一整天也就不需要吃东西了。不过今年是第九年,又是孩子走后的第一天,我该一整天好好绘制壁画和伺候鸽子,他想。
他坐在菩提树下的摇椅上吃着乳糜,看着已停止了疼痛的左手腕,“感觉怎么样,手啊?”他问那抽筋的左手腕,它僵直得几乎跟干尸一般。“我为了你在吃乳糜呢。”
我应该在上午把壁画上的鸽子画好。如果来得及,最好把鸽棚打扫一下,也好利用中午的时间给鸽子洗个澡,他想。
中年人习惯于让洗完澡后变得一身清爽的鸽子住进清洁的鸽棚。就像一个在树林中打坐了六年的人跳进河中洗澡,出来后换上一套从未穿过的好衣服一样。
“手啊,你增添点力气吧。像右手一样。”他说。“我需要你做很多事呢。”
我相信它是有潜力的,他想。它当然会恢复元气,来帮助我的右手。有三样东西是兄弟:那条龙和我的一双手,还有这群鸽子。这手一定会复原,并且变好的。真丢脸,它居然会抽筋。
吃过乳糜,中年人开始站在凤的壁画前面画鸽子。他在与凤落梧桐主画面齐平的左上角画了七只正在飞翔的鸽子。由于对鸽子的熟悉,他没用多少功夫就画好了。同时也点缀了几笔这七只鸽子的羽色。信鸽的羽色有很多种,为了避免杂乱,他只选用了两种:他最喜欢的银色和最不喜欢的雨点。遗憾的是在画完之后,银色鸽的羽色在墙壁上看起来就和灰色鸽差不多。
“就这样吧,”他说。“银色也好,灰色也罢,都是我喜欢的羽色。”
可以打扫鸽棚了,他想。
打扫鸽棚是个累人的体力活儿。从前孩子在时,他会帮助中年人打扫。但中年人嫌孩子弄不到点上,只让孩子帮着搭个下手,比如递个东西什么的。孩子在时和中年人说着话,干活不会让他感到累,不知不觉就干完了。
“要是孩子在这儿就好了,可以助我一臂之力,”他说出声来。
谁也不该过了中年还一个人待着,他想。不过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为了保养体力,我一定要记住在每次打扫鸽棚前多吃一点乳糜。记住了,不管你想吃不想吃,都必须吃,而且在早上吃。记住了,他对自己说。
中年人照例先将早上放出后已进棚的鸽子再次放出,留下正在孵蛋的那对种鸽和让孩子拿走配对雌的那只鳏夫雄鸽。像这些不能放的死条①鸽子,从前在中年人打扫鸽棚和为其洗澡时,由于他的大意,曾从棚中溜出一去不复返。也许,我和这些鸽子的缘份已尽吧,他想。他将棚中的每只鸽子都看成是今生和自己结的缘。
(注释:①为了做种和防止逃跑,从别人那里引进的成鸽,终日关棚饲养,鸽界统称为死条。)
中年人今天在打扫鸽棚时,依旧是先清扫地上和鸽巢以及角落里的粪便,然后再用抹布擦拭塑钢门窗。在擦拭门窗时,他会将被鸽子踩上鸽粪的脚沾染得污迹斑斑的滑槽,用钢刷蘸上消毒液清除干净。然后用蘸上清水的抹布擦拭。最后再用抹布擦干。这在别的鸽友是不屑于去做的。
类似打扫鸽棚一样,在为鸽子洗澡时,中年人同样会多做一些工作。
这时候,他会取出一些草药百部用少量的井水泡在锅里,然后再从井中汲一桶水上来。在百部泡有一个小时之后,他将泡有百部的锅添满水放在火上反复煮沸。半个小时后关火。不掀盖再闷一会儿。掀盖后放凉,倒入浴盆中与大部分原生井水混合让鸽子洗浴。这样做的结果是富含矿物质的井水直接作用于鸽子的身体,能使其迅速恢复疲劳(尤其是对那些参赛归来的鸽子更适合)。同时草药百部的消毒作用不仅对鸽子的身体无害,还能起到杀灭寄生在鸽子身上的病虫害的保健作用。别的鸽友在含有氯气的自来水中放入高锰酸钾让鸽子洗浴,却以为经过化学药品消毒的自来水里面,再放入用于给鸽子消毒的化学药品,这双重功效的杀菌防护总该对鸽子的身体有益吧。
中年人给鸽子洗澡用的浴盆是自制的,呈长方形,木质的。它倒入水后就像是一只漂浮在海上的船。
在菩提树和梧桐树相互交叉的绿荫下,中年人光着上身,穿着一个胖大的短裤,手摇芭蕉扇躺在莲花摇椅上,看着在院子中央的浴盆中纷纷跳入又跳出的鸽子。那些已洗过澡的鸽子正三三两两的散开羽翅卧在地上舒服地晾晒湿漉漉的羽毛。
正午已过,阳光变得越来越强烈。不知怎么回事,这几天的气温骤然升高,超过了往年同期的正常值,达到三十七度。往年只有在七月份才会出现这样的高温。
也许是中午的热浪迫使人们都躲在了有空调的屋子里睡午觉,这一会儿院外鼎沸的人声沉寂了许多。只有不时来往的汽车在提醒这个世界还有声音的存在。在汽车过后短暂的间隙,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几声蝉噪更加衬托出午后的寂静。
在院中,鸽子的洗澡也引起了在两棵树上筑巢的鸟儿们的兴趣。好动的喜鹊嘎嘎地叫着,翘动着长尾巴,树上树下地飞来飞去。安静的斑鸠则围在浴盆旁边好奇地看着鸽子洗澡。不知从哪里来的麻雀也赶来凑热闹,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墙头屋下地蹿来蹿去。那几种不知名的鸟儿也不安份地鸣叫着在院中乱飞。鸟儿的叫声与鸽子咕咕的叫声和鸣在一起,衬出午后燥热空气中流淌的静谧。.
中年人很高兴,他有这许多相邻的朋友来做伴。
“那条龙也是我的朋友,”他说出声来。“我从没见过或听说过这样的龙。不过我必须把它画活。我很高兴,我们不必去画活那些麻雀。”
想想看,如果人必须每天去画活麻雀,那该多糟,他想。麻雀会越来越多。不过想想看,如果人必须每天去画活喜鹊,那又怎么样?我们总算生来是幸运的,他想。
于是他替这条墙壁上干待着的龙感到伤心,但是这种伤心并不能减弱要画活它的决心。它能供多少人欣赏啊,他想。可是他们配欣赏它吗?不配,当然不配。凭它的气宇轩昂和深藏不露来看,又有谁配欣赏它呢?
我搞不懂这些事儿,他想。可是我们不必去画活麻雀或喜鹊,倒是好事。在凡间过日子,画活和养活自己真正的兄弟已经让我们感到重负在肩了。
这时候院中突然刮起了西南风,干燥的热风让他认识的鸟儿一只只地躲回了树荫里。麻雀也飞走了。洗完澡已晾干羽毛的鸽子都接二连三地钻进了鸽棚。眼下他仿佛正躺在一块沙漠中的绿洲里。
他起身将浴盆中鸽子洗浴之后的水倒掉,又将浴盆洗刷了一遍放回原处。然后他站在院子中央手搭凉棚,眯缝着眼睛抬头仰望了一下被灼热的阳光笼罩的天空。然后他重又躺在了树下的摇椅上。
他凝视着院落,发觉他此刻是多么孤单。但是他可以透过树丛间的缝隙看见鸟儿来回穿梭的身影、风吹树叶响起的哗哗声。
由于西南季风的吹动,天空中的云块正在飘散或聚积起来,他朝上望去,见到一行白鹭在飞行,在青天的衬托下,作为侯鸟的白鹭又回到了北方,开始在这个城市高高的梧桐树树梢上筑巢和繁衍,于是他明白,一个人在院中是永远不会感到孤单的。
他想到有些人开着车驶到了望不见人烟的地方,会觉得害怕,这是因为他们担心在那几个月里天气会突然变坏。他们是有理由害怕 的,因为现在的天气确实是说变就变。以往这个城市从来没有刮过飓风,而现在,飓风不知何时就不请自到了。如果在不刮飓风的时候,这些月份正是一年中天气最佳的时候。
在飓风来临的前几天,如果你正在旷野的话,你可以看见天上出现的种种迹象。人们在楼宇里却看不见,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找什么,他想。在室外一定也能发现异常的现象,那就是云变化的形式不同。眼前看来,不久就会刮飓风。
他望望天空,看见在高高的上空,在呈现出青色的五月天空的衬托下,一朵朵白色的云团,形状像一座座飘浮在蓝色大海上的冰山在移动。
“天气在三四天内会发生变化,”他说。“但是今晚和明天还不会有什么事。我应该睡上一觉,单身汉,睡它一会儿,晚上再去浴池洗个澡。我有些累了。龙只有等到明天去画了。”于是他入睡了。
他没有梦见大鸟,却梦见了几条大鱼鲲,伸展于海天相连处,在这个正值它们发情的季节里,雄鱼常常会兴奋地跃起半个身子于海面上,然后又会起劲地追逐起雌鱼。
在这以后,他梦见那道长长的稻田土埂和隔着沟渠的小树林,看见第一只大鸟在傍晚时分掠过树林上空,接着其它大鸟也来了,于是他放下画板,不再作画,晚风吹向树林,他等着看有没有更多的大鸟来,感到很快乐。
这天晚上,中年人没有睡在院中的摇椅上,而是睡在龙池的床上,一张靠近窗户的床上。他经常在这家全天营业的浴池洗澡并过夜,喜欢在夏天睡在靠窗的那张床上。这样他就能透过窗户,从有些闷热的浴池大厅触到来自于室外的清新空气。
他每想到大地,老是称她为母亲,这是人们对大地抱着好感时用汉语对她的称呼。有时候,对大地抱着好感的人们也说她的坏话,不过总而言之还是把她当女性看待的。有些较年轻的鸽友,用环标当鸽脚上的足环,并且在把种鸽的后代卖了好多钱后置备了汽车,都管大地叫坤,这是表示男性的看法。他们提起她时,把她当作一个对手或一个归宿,还有的甚至把她当作一个敌人。然而这中年人总是把大地当作女性,她常常吝于或者不愿付出,如果她做事轻率,不顾后果,那是因为她天生如此。因为太阳对她起着影响,她由不得自己,如同对一个女人那样,他想。
他舒服地睡着,这种沐浴之后就躺在床上的生活,让他好好保持在自己的最佳状态以内,而且除了偶尔微风掠过窗外,响过一阵汽车车轮轧过马路的声音,大地是平静无事的。他很快就睡熟了。他什么也没梦见,只梦见一只黑色的大鸟飞向远方。他正让清风帮他干信使的活儿,这时天渐渐亮了,他睡醒时发现自己已经睡到比预期活着能梦到的地方更远了。
我在那画有龙的墙壁前面对了一个月,可是一无所为,他想。今天,我要画出那长有鱼鳞的蛇身和四只兽脚。至于那双眼睛,说不定点上就会活起来。那么,没有了赖以藏身的云海,这条已有了全身的龙还会在墙上待下去吗?
太阳还没有从地平线上升起,中年人提着洗澡用的兜儿从龙池出来。
一架飞机在他头上飞过,正顺着航线飞向南方,他看着它的影子惊起成群成群的乌鸦。
有这么多的乌鸦,那里该有树林,他想。经过一天零一夜的飞行,不知道孩子乘坐的飞机到了希腊没有。也许还没有。走在回家的路上,他注视着飞机,直到它消失在视线以外。
我没有坐过飞机,坐在飞机里也许感觉很怪,他想。谁知道从飞机上俯瞰,陆地会是个什么样子?海洋又是个什么样子?如果能飞得低一些,他们说不定能清楚地看到那条龙。我希望在三百米的高度飞得像滑翔机一样慢,从空中看龙。在掏鸟蛋的野外,我攀在树顶鸟巢旁,即使从那样的高度也能看到不少东西。从那里朝下望,斑鸠的颜色更土,你能看清它们脖颈上的黑色斑点和身上的条纹,你可以看见它们常常雌雄结伴在觅食。弄不懂,凡是在深山的树林中飞得很快的鸟都有黑色的背脊,一般还有黑色斑点或条纹?斑鸠在树林里当然看上去是土色的,因为它们实在是褐色的。但是当它们饥饿难耐的时候,浑身羽翼就会出现黑色条纹,像龙那样。是因为什么才使这些条纹显露出来的呢?难道是因为愤怒,还是飞得太快?
“龙啊,”他说。“我除了爱你,还很尊敬你。我今天非要把你画活不可。”
但愿今天能把此事了结了,他想。(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