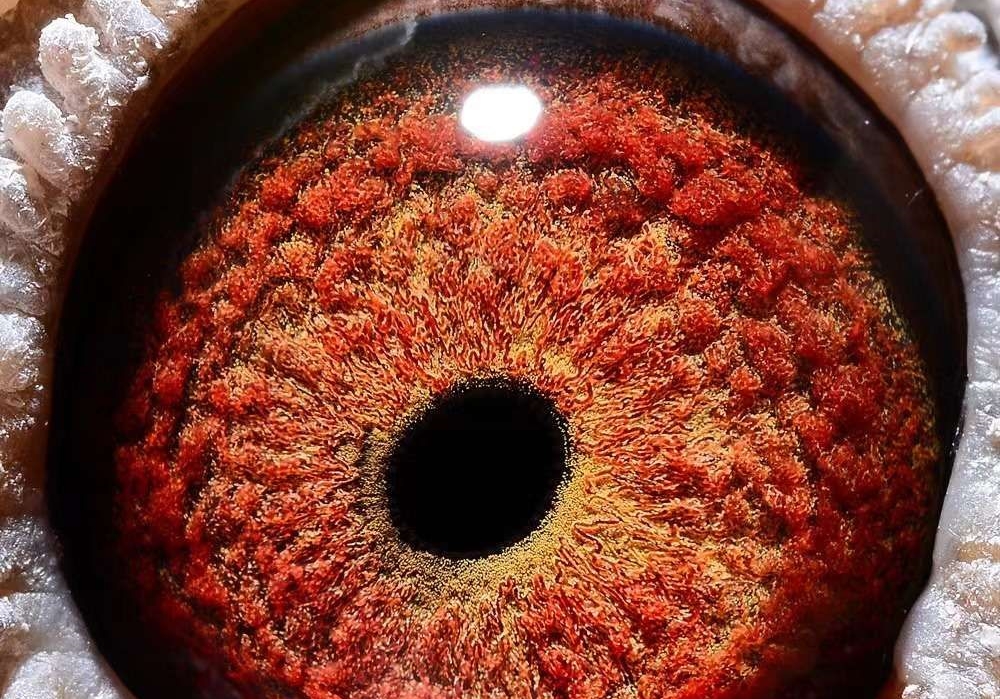认识了欧阳铁权以后,我的心里亮堂了,我似乎看到了中国信鸽运动的春天已经不远了,我甚至不在乎铁姐那边了。
现在想起来,我真单纯。
如今,整个地球沙尘暴肆虐,沙尘暴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灾害,单靠欧阳和我们几个栽几棵小树,就能抵挡住凶残肆虐的沙尘暴?
混乱的鸽界也是一样,已经到了不能再混乱的程度了,单靠欧阳和我们几个的力量实在是势单力薄,拯救鸽界需要广大鸽友们的警省,需要全社会的重视。
当然,我的这种认识是以后才悟出的。
……
认识欧阳的第二天,也就是在翔子家楼盖上和欧阳他们喝酒的第二天,我终于接到了耿秃子的电话。原来,前些日子耿秃子被人民法院行政拘留了。原因是因为他和六哥的官司,他以败诉而收场。耿秃子从心里往外地屈呀!他真的是一文钱不欠六哥的,可是,六哥出据有他按的手印的欠条,在法律上是份再有力不过的证据了,他真的是哑巴让驴操了,啥也说不出来。有生效的人民法院的判决,耿秃子无奈了,他只有想通过跑路想跑黄这笔债。可是,最终他还是被抓了,由于他拿不出100万,所以被行政拘留了15天。昨天才放出来,据他说是东拼西凑凑了20万后,做了个还款计划才被放出来的,而且人民法院限定他在半月内还清所有欠款,不然还要有牢狱之灾。耿秃子算计别人一辈子,到头来让六哥算计了,这小子比窦娥还冤呀!
耿秃子给我打电话,当然还是拍卖的事。怪不怪,这小子一百个信任我。他说他已经想好了一整套的拍卖方案,想约我去北京跟他详细地谈谈,这小子怕再次被抓,一杆子跑北京去了。我感到机会终于来了,耿秃子呀耿秃子,你相信谁也不应该相信我呀!我是谁?我是你的克星呀!我找机会祸害你还找不到呢,你小子真的往枪口上撞。当然,我答应了他。
我决定去北京与耿秃子见面。
途中,我想去看看雷伯,老人家一定很寂寞,我一定陪老人说说话,告诉老人省鸽协来了一位一身正气的秘书长,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鸽界的希望。我想,看完雷伯后,我一定要去蛇山子看望一下二叔、麻三他们,还有姗姗现在在干什么?媚姐是不是已经回美国了?我真的是从心里想他们呀!
本来我打算好好的,坐早晨6点钟的火车,中途去看雷伯,然后去蛇山子看二叔他们,再坐当天晚上9点的火车,次日早晨正好到北京。可是,事实上我的行程因为妻子而发生了改变。
儿子被六哥他们绑架以后,妻态度坚决地阻止我停止一切与鸽子有关的行动,坚决反对我去北京。于是,我们开始了冷战。当我决定次日起程去北京时,我写了一张字条放在了她的床头,字条是这样写的:我明天坐早晨6点的火车去北京,请5点叫我起床。我觉得妻虽然阻止我一切与鸽子有关的行动,但是,她心里明白,她是没有办法阻止得了的,因为她太了解我了。可是,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样,第二天我一睁眼,快8点了,妻早已上班走了,想不到妻她真的没叫醒我。我转身发现我的床头上竟然也出现了一张妻写给我的字条,字条这样写:5点了,起床吧!
我真是哭笑不得,我理解妻。
没办法,我只好爬起身直奔火车站,赶上哪趟车坐哪趟车吧,反正我又不是去赶考,早点晚点无所谓。
来到了车站,我突然发现今天的火车站人山人海,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人呢?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一打听才知道,北京那边马上就要召开人代会和政协会,为防止上访户进京上访,信访部门调动相关部门搞人海战术,在车站控访。控访?换言之,就是控制上访吧。我一百个搞不明白,高度民主、高度法治、构建和谐社会的国度里,为什么要控制老百姓上访呢?我觉得这和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实质相违背。我觉得,上访非但不应该控制,反而应该打开一条通往上访的绿色通道。对那些有冤屈的上访户,一定要想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对那些无理上访、缠访、闹访的上访户坚决打击。
或许因为我站的角度不同,问题想得过于简单,但是我想,也没那么复杂。
我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有些事情不是我想的,想也想不明白。费那脑筋没劲,还不如想想下一步怎么对付耿秃子呢!
我经过了买票、进站、上车三道防线严格的审查,终于登上了火车。很多人没能像我这么幸运了,不一定在哪道关口就被堵截住了,控访者真厉害,一眼能发现谁是上访的。我真看不清上访者长什么样。
……
我下车时,天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了小雨,好像是今年春天的第一场雨。
我冒雨向雷伯的坟墓走去。
当我接近雷伯的坟墓时,我突然发现有一个人正立在雷伯的坟墓前,任凭风吹雨淋,久久地站在那里,跟雷伯说着什么。
我看清了,是曲勇。
我没有马上打搅曲勇和雷伯说话,而是静静地站在一旁,听曲勇跟雷伯说话。
曲勇说:“雷伯,我上次跟您说过,公棚比赛完拍卖时,我在鸽友面前只讲了两句话,就是搞好奖金赛,将奖金赛进行到底!您说得对,赛鸽比赛,如果形式上都能不公正,何谈实质公正呢!放心吧,雷伯,我是不会让您失望的。尽管现在鸽友们对奖金赛表现得还很麻木,但是我想只要我们不懈的努力,我们会成功的!对了,雷伯,我们省鸽协新上任了一个秘书长,是个一身正气的年轻人,他和我们一样,对普及奖赛很有信心……”
曲勇的话音未落,天空中炸响了一声春雷。
曲勇接着说:“春天来了,赛鸽运动的春天也一定不会太远了。”
曲勇话说得很有力,听得出,是发自心底的声音。
曲勇接着说:“雷伯,军师这小子真行,前几天他儿子被六哥他们绑了,还好,最后他儿子安然无恙。这小子没有被吓倒,继续痴心不改,昨天他和我通电话,又要去北京,他要粉碎耿秃子的阴谋,阻止耿秃子以拍卖为由坑害那些仍然麻木的鸽友。”
雨,还在没完没了地下着。
我静静地走上前,轻轻地拍了拍曲勇,没有语言,一切都在不言中。
曲勇回头看了看我,然后对雷伯说:“军师来了,他来看您来了。”
我深深地向雷伯鞠了一躬,然后说:“雷伯,我想您了,想陪您唠唠喀,想说的话曲勇都说了,您就安息吧,不久我们会给您带来好消息的。”
……
雨,还在下着。
春雨,滋润着大地,滋润着人们的心田。
……
离开了雷伯,我要去蛇山子,想约曲勇一起去。
曲勇笑了,他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
于是,我们分手了。
由于我的行程被妻打乱了,所以,当我赶到蛇山子时,已经是黄昏时分。
来到蛇山子,我得到的第一则消息就是姗姗突然不见了,去哪儿?去干什么?什么时候走的?麻三他们一概不知道,就连媚姐也不清楚。
是呀,姗姗她会突然去哪儿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