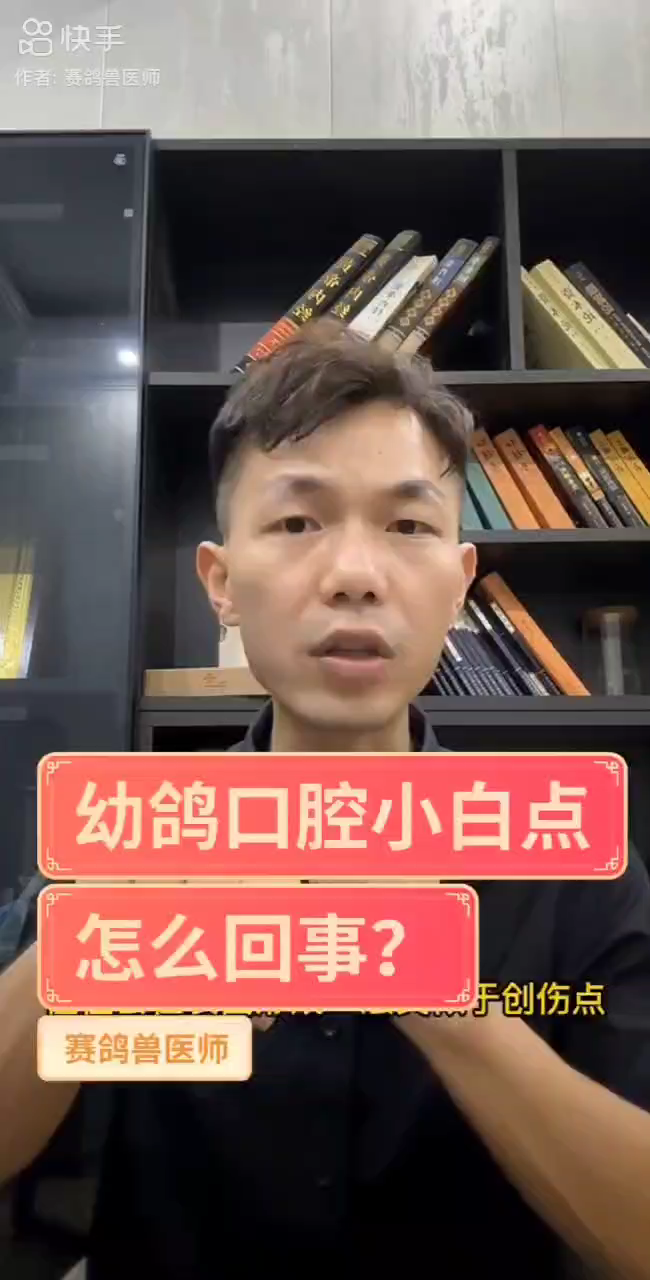倘若在一个小圈子里狗扯羊皮也就算了,竟然还大言不惭褪去作家外衣,以记者自居。想想那身记者行头是怎么得来的,还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因为爱鸽子,才写鸽文?我就不在意那些损我是武昌火车站搬运工的留言。即使我现在还干着份清闲舒适,衣食无忧的工作。呵呵!
在我看来,以何种手段为生并不是判断人的标准。人无贵贱,人的思想有贵贱。有些人即使每天洗澡,他们也洗不净体内流淌的肮脏的思想。只要思想是干净的,即使是妓女也值得我们推崇。香港电影《性工作者十日谈》中,有这样一个妓女,名为“happy”,她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做一名快乐的妓女,热爱性工作者这份职业,只是难免有点逼迫自己苦中寻乐的辛酸。真没想到,这种苦中作乐的辛酸,也被人套用到鸽事作文、作人上来。他们如独裁者大喊我最代表人民,贪官们人模狗样地讲要打击腐败,教授们说坚守道德和良心。看他们表演的时候我真有恶心的感觉,我就知道什么叫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却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了。
看这些人的赛鸽文字,如梗在喉,哑然失笑。文章让人读罢,窝心的同时还能把人气乐,我不得不佩服该文作者很有才。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告诉《财经时报》记者,现在,市场标准取代了文学标准,精英作家和汉语整体水准都在下降。朱大可说,他希望看到的是既有市场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出现,“只有这样,作家才不会沦落为文学二奶,才不会有生存危机,也只有这样,文学才能进步。”朱大可也因此获得了一些声誉。他的“这个世界需要的决不再是创造思想的精英,而是追踪公众趣味与理念的猎狗”的言论,更是叫人清醒到冷汗淋漓。
时下某些写鸽文的最经不起批评,有批评就说是人身攻击,有赞扬便飞扬跋扈,这是可以理解的。不可理解的是圈中人几乎听不到不同言说,他们不是失明就是失语,抑或失聪。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些作家、记者们可以大言不惭地“为赋新辞强说愁”,操练文字游戏,以证明自己不俗。全然忘记了鸽文是要依靠“在鸽棚里亲手铲鸽粪”支撑的。记得十几年前,国内几位风头正劲,指点江山的鸽文写手何其锋芒!我的一位好友“赛前说话”——这些人迟早会被鸽圈淘汰,甚至连鸽子都不会养了。我在惊讶之余追问为什么?回答是,这些人其实关心的不是鸽子,而是与鸽子发生关系的人。一个养鸽人,通过文字在圈中成名,并把这当作唯一的捷径,不管现时多风光,退出这个舞台,只是早晚的事情。现在再看那些曾在鸽文领域风骚多年的文豪快手,早己是人去棚空,寞寂无闻。
投身赛鸽文字,是纯粹而又艰难的劳动、当能够学会像农人忍受饥饿、曝晒、寒冷、大风、疲惫、旱涝灾害的打击那样忍受焦虑、脆弱、困惑、迷惘、慵懈的困扰和煎熬,日复一日地进行韧性地劳作,最终一丝不苟地将自己心灵和思想的话语填满稿纸的每一个格子时,这才是推动鸽界进步的责任。居然还有人说为了写鸽文可以不养鸽子;写了鸽文就可以以文易物,写了鸽文就可以叫赏识的老板花几万为你买鸽!市场诱惑和生存压力,真的不用耐住寂寞一边育赛,一边烹文煮字,写出流水帐式的应景之作就算是无愧于时代和鸽界发展的赛鸽文字?
诸葛孔明在舌战江南群儒时说:“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心中实无一策。”这话击中了中国某些文人和知识分子的要害,但也实在是太尖刻了。我真的看不惯那些“满嘴主义,满肚子生意”的鸽事作家记者们,他们就像一个不入流戏子,虽然自知演技很蹩脚,但仍然不时的像台下张望。期盼能有几声哪怕是稀稀落落的掌声也好。呵呵,只要一个眼神肯定,自己卖力的表演也有意义。
英雄本色里小马哥说过一句话:不要以为看了几本书,就可以混黑社会了,你试过被人用枪指着头,喝完整瓶的威士忌吗?不要以为能写几篇鸽文,就名满天下,快意人生,为所欲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了!这让我想起中国历史上那个著名的北齐亡国皇后胡太后。当她因亡国从从幽闭的皇宫中来到外面的花花世界,要是换作他人,可能会选择自杀而免辱。意外的是,胡太后竟然和她的儿媳妇,一起到长安城里的妓院,兴高采烈地当起妓女来。胡太后快活地对儿媳妇说:“当后何如当妓乐”。做妓女不必像做皇后、太后一样,要假装高贵,假装矜持。原来,写鸽文快乐至上的源头,来自于斯呀!
回首中国大陆的鸽界文字圈,历经一穷二白,什么都不懂的文盲时代;再到观点撞碰,文征笔阀的文痞时代;及至以文易鸽,以文易钱物的文丐时代,到如今己昂首阔步走向快乐意淫,财色兼收的文妓时代。胡太后快乐至上的灵魂早己附体各位鸽界文豪大腕。鸽文写作目的和为文风格已显露出“当后何如当妓乐”的人生理想。我更加相信,他们可以让现在所有的“鸽文记者”相形见拙,让鸽坛上所有的文字黯然失色。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